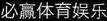新中国成立以来,城市工作会议一共召开过四次,分别是1962年、1963年、1978年、2015年。它是城市工作领域规格最高的会议,且每一次会议召开,都处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。
从1962、1963年应对经济困难时期的城市调整,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启动,再到2015年新型城镇化战略,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不断演进,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和所面临的问题也随之变化。
当前,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7%,城市发展正式迈入存量时代。在此背景下,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,将对新一轮城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?
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阶段性跃迁,折射出全球城市化“诺瑟姆曲线”的普遍规律——当城市人口超过30%后,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;超过70%后,进入城市化后期阶段,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下降。
“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、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,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1%提高到2024年的67%。”
但转折点已经到来。数据显示,2011-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.39个百分点,2021-2024年降为0.78个百分点,增速明显放缓,预计未来还将继续下滑。
而逼近70%的拐点阈值,标志着一个周期的结束。对此,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:
“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,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。”
这一转变不仅是阶段的转换,更是城市发展逻辑的重构。最直接的改变是,“土地财政+房地产”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。
过去几十年,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,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。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征地、出让土地获取财政收入,以此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。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,城市边界不断扩张,呈现出摊大饼式的发展态势。
这种模式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了城市规模,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爆,解决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,但也带来了土地资源浪费、房价泡沫、债务风险加剧等一系列问题。
如2015年城市工作会议后,棚改货币化政策拉开大幕,房地产行业高歌猛进,楼市繁荣背后是房价的一路飙升。
如今,随着城镇化增速放缓、人口结构转变,住房需求峰值已过,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。简单来说,买房的人少了,地也卖不动了。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.6%,2024年进一步下降10.6%,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,房地产驱动的土地财政这台发动机正逐渐减速。
此次会议特别提出“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”,这一表述与以往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”有所不同,其核心在于切断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。
在房地产层面,未来的土地供应必须从无限供给,转变为按需求定供给;在城市发展层面,不能再依赖房地产开发来维持财政增长,而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,如科技创新、产业升级等。
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,还是优先发展大城市?这一命题在中国的城镇化历程中几经摇摆。
比如上世纪80、90年代的《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》《城市规划法》等文件都提出,“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,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”。
然而,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和户籍门槛的松动,大量人口涌入城市,向大城市聚集,按照旧的人口标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已不切实际。
另一方面,考虑到人口、技术、资本等要素的集聚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,大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要阵地。
如2019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到,“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”,“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”。
按照2014年发布的新的城市划分标准,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的为中等城市,100万以上的为大城市,500万以上的为特大城市,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。
到目前为止,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重庆、广州、成都、天津7个城市,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,为超大城市;武汉、东莞、西安、杭州、佛山、南京、沈阳、青岛、济南、长沙、哈尔滨、郑州、昆明、大连、苏州15座城市,城区常住人口500万—1000万,为特大城市。
然而,政策倾向于大城市优先,导致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二线城市,引发了人口过度集聚、房价高企、公共服务压力巨大等一系列“城市病”。
因此,近几年我国的城市发展策略,开始再度转向,从大城市优先回归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,着手纾解大城市的非核心功能。
此次会议明确,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,“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,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,促进城乡融合发展”。“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”,再次被摆在重要位置。
但需要指出的是,协调发展要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,并非简单的资源平均分配,而是通过城市群、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,带动中小城市,同时激活县域经济。
会议强调,“发展组团式、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”,核心要义是,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,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。
目前,全国共有19个城市群,30多个都市圈,但各城市群、都市圈的融合发展水平参差不齐。
长三角城市群、粤港澳大湾区、京津冀城市群等,相对来说,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济联动机制,基础设施互联互通、产业分工协作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较高。
如长三角地区已实现高铁“1小时通勤圈”,以及“上海研发+外地制造”协作模式;粤港澳大湾区则是“香港金融+深圳科技+东莞制造”产业链整合模式,且广佛都市圈早在十多年前,就开通了全国首条跨市地铁。
“发展组团式、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”,旨在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,推动一体化进程,加速资源集聚,通过城市群、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,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。如昆山之于上海,中小城市可以通过产业分工,融入大城市的产业链中。
长期以来,不少人认为,打破行政壁垒,会导致资源过度集中流向大城市,加剧城市发展的马太效应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,当前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,并非过度市场化所致,而恰恰是市场化和一体化水平不够高,各城市利益不同、互相博弈,同质化竞争,尚未形成高效联动融合机制。因此,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,仍需进一步拆除城市间的壁垒。
在城市群、都市圈之外,县域经济的激活,也是平衡区域发展、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抓手。
七普数据显示,2020年我国县域常住人口约7.48亿人,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.97%。在数量繁多的县城中,昆山、江阴、张家港等百强县(市),终究是少数,绝大部分县城发展水平欠佳。然而,它们却是人口流动的重要中转站。
很多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后,受制于大城市的高房价和物价,最终返乡后,可能会选择在县城安居。这一趋势既缓解了大城市的承载压力,也能促进区域平衡发展。
当然,“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”,关键在于,县城要找准定位,找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道路。如大城市周边的县城,可以积极做配套产业分工;有资源优势的县城,可以做大特色产业。
在存量时代,城市间抢人竞争加剧,中小城市和县城会等下沉地区,面临更大的发展压力。但人口流动新趋势下,中小城市和县城并非必然衰落,关键还是找准定位、培育特色。
过去十多年,移动互联网的加速普及,将“淘宝村”“直播镇”带进了偏远地区,进一步推动了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。一些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,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得了发展机会。
此次会议将“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”,列为七大重点任务。这一部署背后,是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物联网等新技术,正以更快的速度改变城市发展模式。尤其是人工智能,正从技术工具升维为城市治理的新操作系统。
此前,“杭州六小龙”火爆全网,其诞生体现了城市发展的创新活力。反过来看,AI领域的发展,也会给城市提供技术创新积累,帮助占领未来的风口前沿,成为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。
另一方面,AI技术在城市治理、交通管理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应用,使得城市运行效率大幅提升。
随着土地财政式微,房地产发动机减速,未来的城市的竞争,将不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和土地资源,而更依赖于科技创新能力和数字化水平。
麦肯锡全球研究院(MGI)发布的报告指出,未来15年AI等行业将成为驱动增长的核心引擎,预计贡献29万亿至48万亿美元的收入,占全球GDP增量的1/3,并重塑技术、资本流动与产业迁移的格局。
在存量时代,创新要素如人才、资本、技术,仍将集中在大中城市,人工智能将放大这些城市的竞争优势。但正如互联网的“平权效应”一样,中小城市同样有机会分享技术红利。
如“东数西算”工程,可以通过重构算力、能源与数据的空间配置,激活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,破解发展不均衡问题,为欠发达地区带来新的增长机遇。
从高速增长到稳定减速,从土地财政依赖到创新驱动发展,从大城市优先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、县域经济崛起,城市发展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。人口流动趋于平缓,技术创新却在加速扩散。
在城市发展全面转向提质增效的新时代,谁能率先把技术曲线转化为治理、产业优势,谁就能在下一轮城市竞争中赢得先机。bwin官网